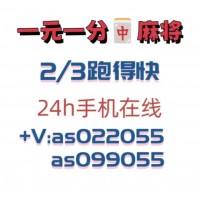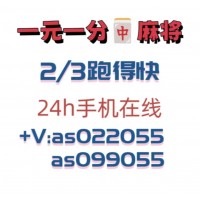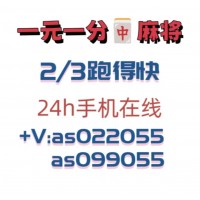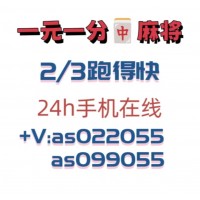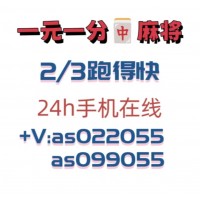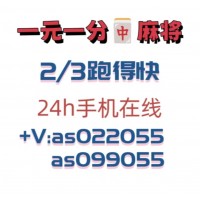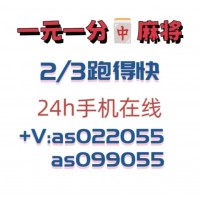2004年1月,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皇皇九大卷《余光中集》,受到广泛注意;2004年4月,备受海内外华语文学界瞩目的第二届“华语文学传媒大奖”开奖,余光中成为2003年度散文家奖得主
近日报刊上关于他更是连篇累牍,“文化乡愁”、“中国想象”、“文化大家的风范和气象”之类的溢美之辞让人头晕目眩
今年4月21日的《新京报》上,一位记者在其“采访手记”中这样写道,“高尔基提前辈托尔斯泰‘一日能与此人生活在相同的地球上,我就不是孤儿’,况且曾相见并有过一夜谈呢?”他将余光中比作托尔斯泰,并为自己能见到这位大师而感到幸运万分,这段“惊艳”之笔将大陆的“余光中神话”推到了极端
遗憾的是,这些宣传和吹捧说来说去不过是余光中的“乡愁”诗歌和美文,而对余光中在台湾文学史上的作为毫无认识,因而对于余光中究竟何许人并不清楚
不过,对于普通的读者也许不应该苛求,因为大陆对于台港文学一向隔膜,而余光中又善于顺应潮流
举例来说,在九大卷300余万言的《余光中集》中,余光中的确是十分干净和荣耀的,因为他将那些成为他的历史污点的文章全部砍去了,这其中包括那篇最为著名的被称为“血滴子”的杀人利器《狼来了》
但在行家眼里,这种隐瞒显然是徒劳的,每一个了解台湾文学史的学者都不会忘记此事,海峡两岸任何一本台湾文学史都会记载这一桩“公案”
乡土文学之争 余光中在台湾文坛上的“恶名”,开始于“唐文标事件”
70年代初,台湾文坛开始对一统台湾文坛的“横的移植”的现代主义诗歌进行批评反省,其标志是唐文标先生的系列批评文章,他在1972年到1973年间的《中外文学》、《龙族文学评论专号》、《文季》等刊物上先后发表了《先检讨我们自己吧!》、《什么时代什么地方什么人》、《诗的没落》等文章,批评台湾现代诗的“西化”和脱离现实的倾向
这一系列文章在文坛引起了震动,引发了关于现代诗以及现代主义的大争论
在这场论争中,余光中当时是维护现代诗的代表人物
关于论争的是非本身,这里无需加以评判
想提到的是,余光中一出手就显示出他的不厚道
在《诗人何罪》一文中,余光中不但言过其实地将论争对方视为“仇视文化,畏惧自由,迫害知识分子的一切独夫和暴君”的同类;而且给对方戴上了在当时“大陆”的台湾最犯政治忌讳的“左倾文艺观“的帽子
所以就有论者揭露余光中搞政治陷害,如李佩玲在《余光中到底说了些什么》一文中指出:“这样戴帽子,不只是在栽害唐文标(也算得上是压迫知识分子了吧),还在吓阻其他的人
” 但这样的批评对于余光中没有产生什么效果,在70年代后期著名的台湾乡土文学论战中,余光中变本加厉地施展了他的攻击手段,并且与国民党官方、军方配合申伐左翼乡土作家
在这场乡土文学论战中,台湾乡土文学受到的最大攻击来自两个人,一个是代表官方的国民党《中央日报》总主笔彭歌,另一个就是余光中
在乡土作家看来,最为可怕的并不是彭歌强调“”的官方言论,而是余光中关于台湾乡土文学“联共”的诬告
1977年7月15日至8月6日,彭歌发表了系列官方文章,强调“爱国是基本的大前提”,不是“蹈入了‘阶级斗争’的歧途”
紧随其后,余光中在8月20日《联合报》发表了《狼来了》一文,影射台湾乡土文学是大陆的“工农兵文艺”
他在此文开头大量引述了毛泽东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的观点,以此证明台湾乡土文学的思想与前者的相类,并且说:“目前国内提倡‘工农兵文艺’的人,如果竟然不明白它背后的意义,是为天真无知;如果明白了它背后的意义而竟然公开提倡,就不仅是天真无知了
”接着,他从攻击大陆的共产党文艺统治谈起,抱怨台湾的“党治”未免过于松懈,对于乡土作家过于客气: “
儿子来到微信,摇曳,声音有点愚蠢,感冒,必须吃药
可以连接到前面,老朋友,我仍然想到,我会不可避免地,我想有一个评论和文章评论,两个不正确
最终,仍然在夜晚,这个深刻的道路光,它似乎有♥,我喝醉了,生活并不后悔
当我打起来时,我跳到了我的眼里
朋友们,你想思考它,真的不是,每个人都很乐意分享,文字和文学,悠闲,雅杰,幸福快乐永远是永远的,晚安睡个好觉
11、记住了,自己喜欢的东西,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看
喜欢胜过所有道理,原则抵不过我乐意
立秋收夏色,轻雷模糊地穿梭七弦琴润长安之蒙蒙小雨,滴答滴答地清醒窗外婆娑树影透过帘栊,与几案上的七弦琴弦订交甚欢,犹如稀世宝物,风荷摇思俯身盘弄七弦,只听得玉鸣铮铮,盖过了檐下小巧精致雨声
真的,内心一直很庆幸自己,当年能够选择那个行业,毕竟,建筑系桥梁专业的生涯,给我生命中留下了许多难忘的岁月
而往往,在青春的时光隧道里,那些第一次,都让我得到了许多或恐惧或美好的回忆
以上就是关于信誉保障1元1分红中麻将跑得快群的那全部的内容,关注我们,带您了解更多相关内容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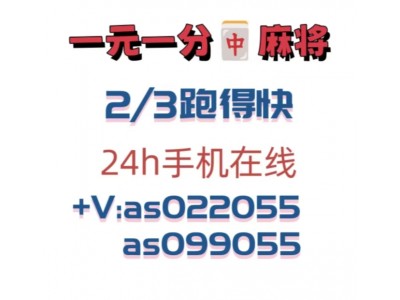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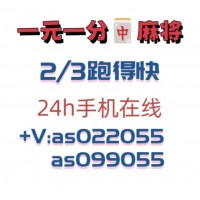


 [VIP第1年] 指数:1
[VIP第1年] 指数:1